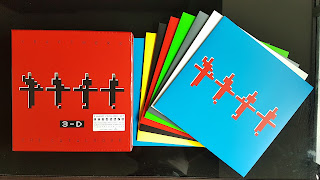(2008.11)
來自德國Düsseldorf的傳奇性電子流行音樂教父Kraftwerk將於
12月5日訪港舉行其Live in Hong Kong音樂會,對於全港的電子音樂愛好者而言,大家都不禁大呼夢想成真,畢竟大家過去都從沒料到Kraftwerk會有登陸香港這塊彈丸之地演出的一天。
與此同時,那亦造就了我跟其靈魂人物Ralf Hütter進行對話的好機會,那簡直是在短期內給我實踐了兩個以往視為不可能的夢想。須知道Kraftwerk並不熱衷做訪問,可以跟Ralf對話,絕對有「執到寶」之感。
Kraftwerk對我的影響甚深遠,沒有當年Kraftwerk予我的音樂啟發與衝擊,也沒有今天的我。友人笑言我訪問Ralf Hütter,可謂儼如「與神對話」。雖然只是一次電話訪問,但我已有未出發先興奮的心情。而心情有點緊張,因為是要在有限的二十分鐘內完成這個訪談——我跟Ralf Hütter專訪,一小時也嫌不足夠啦。
電話線上的Ralf Hütter,並非人們所料般冷漠寡言的藝術家,說話不像機械人也沒有用vocoder跟我對話,反之他顯得相當友善熱情,甚至最後還反問我香港的電子音樂圈大嗎?像不像日本般?
而我也久未寫過一篇訪問稿可以寫得如此眉飛色舞。
啟德機場過境
今年Kraftwerk的世界性巡演只有Ralf Hütter、Fritz Hilpert和Henning Schmitz 三位成員上路,另一主腦Florian Schneider並沒有隨行(但他並沒有離隊),其台上位置由錄像控制員Stefan Pfaffe代替。何以Florian不參與巡演呢?
「他要在大學工作,他已在大學工作了好幾年了。」當然,我們也知Florian不喜歡四處巡演,而寧願留在錄音室工作。
12月5日,將會是Kraftwerk首次來香港演出,但原來曾幾何時,他們也一度踏足過香港,在啟德機場轉機過境。
「我們萬分期待來香港演出。我們曾多次到過澳洲,其中一次便曾在香港的舊機場停站,這是我從前唯一一次到過這地方。現在我們真的要帶同我們的機械人來港了,那是多麼的妙不可言。」
寫過主題曲〈Tour de France〉給環法單車大賽的Ralf Hütter是單車發燒友,不知Ralf可有興緻在香港踏單車呢?
「我不知道呢,哈哈。那要視乎交通情況、多不多汽車而定,也許最好是有單車體育館吧。」
拉闊電音
自2002年秋天一場假巴黎Cit de la Musique舉行的演出起,Kraftwerk正式開始採用四台度身定造的Sony VAIO laptop電腦取替從前台上的笨重電子儀器。現在你們是否很享受作世界性巡演呢?
「當然啦。我們從沒有到過香港演出的另一原因,是我們在80年代所採用的器材太重型了,所有都是analog電子器材,要駁很多很多電線,儀器重量數以噸計。對我們來說,並不可能常作四處巡演,畢竟Kraftwerk是要玩live的電子音樂。然後,自2002年那場巴黎的巡演起,我們首次用上四台laptop作操控,現在我們可以以流動性電子音樂方式讓Kraftwerk周遊列國表演。」
當如今所有音樂人都以用Mac電腦為專業的象徵,何以作為電子先鋒的Kraftwerk卻反而用PC電腦呢?
「對我們來說在技術上而言因為操作PC較良好,正如我所說我要帶著我們的電腦,四處在各種不同的境況下演出,如之前試過一次在日本的寒冷境況,抑或上月在烏克蘭Kiev,我們在晚上於戶外綵排時只有七、八度以下,我們都穿上了絨褸,也試過澳洲的酷熱天氣。而它們的功能仍很好。」
哪次Kraftwerk的演出經驗對Ralf來說是最刺激的呢?
「這是一個持續性的進程,不是只有一個event更一個短短的時刻,而是持續性的。我想我們來得有趣,是因為我們以最大的即興性操控我們簡約的音樂,要專注地去做,以所有藝術性的點子來改變我們的音樂。」
回到1981年的《Computer World》巡演時,在台上四人背後是一座座的電子儀器,但在尖端hi-tech的未來主義techno-pop音樂底下,其實當時他們仍有用上backing tape的。
「所有聲音都是analog的,用的是analog sequence,也用上backing tape播rhythm track與drum track。這是很久之前的事啊。然後我們已有二十多年沒有用過tape了,一切已儲存在數碼器材內,帶來是電腦操控的live表演。」而我亦記得Ralf在另一訪問中憶述,作為一支現場演奏樂團,在80年代他們無法擺脫那複雜的analog科技,令其音樂表演無法跟唱片維持同一層次。
27年前對電腦紀元的想像
Kraftwerk的1974年專輯《Autobahn》公認為首張electronic-pop唱片,毋庸置疑是他們的奠定性之作。然而論到最具前瞻性、智慧性與預言性劃時代意義,是1981年出版的《Computer World》專輯——這是一張對尖端電腦科技作出預告的想像性專輯,對電腦世代作出了精確的預言,也對techno電音、電腦音樂賦予深遠的啟發。但其實那時Kraftwerk根本未有電腦,其典故就是在沒有採用上電腦下而做出很電腦化意識形態的音樂。
「我們製作這專輯,尤其寫歌詞時,我與拍擋產生了這個概念,但我們仍未有電腦,因為在70年代尾與80年代初時,電腦仍很昂貴,只有工廠、大學、電訊公司才可擁有,所以這是一張願景性的專輯。到了那次巡演時,我們才得到首台小型home computer,但也是專輯面世後的事。」他也曾笑言當時只有用這台電腦來打文件與信件而已。
《Computer World》發表的三個月後,IBM的首台個人電腦5150亦在同年隆重面世。那時Kraftwerk已很留意電腦科技的資訊與發展嗎?
「某程度上是有,但更多是來自社會上對人類的處境之推論。Kraftwerk的音樂的關於The Man-Machine,關於人與機器之間的互動。比如早年的Atari小型電腦,我們就是更有興趣於人與音樂機器之互動。」
《Computer World》裡的曲目如〈Numbers〉、〈Pocket Calculator〉,都是關於數字人生。對於今天的金融海嘯,不知Ralf有何見解?
「某程度上,我知道這遲早會發生,畢竟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,是投機生意。我們是較有興趣創作藝術,事實上電腦是可以用作除了賺錢或股票投機以外的東西,它可以創作藝術與音樂,對我們來說的便尤其是音樂方面,我們可以創作合成影象、合成聲音、合成人聲,這都是Kraftwerk所做的。」
初生之犢Krautrock紀元
今年是Kraftwerk的前身Krautrock樂團Organisation成軍四十週年,Ralf有何感覺呢?
「這已是歷史陳跡了,我們只會對未來的有興趣。」
回到60年代末、70年代初在德國衍生的Krautrock運動,看到是德國電子音樂之父Karlheinz Stockhausen的elektronische musik、法國Pierre Schaeffer的musique concrète、英美的psychedelic rock、美國的free-jazz所互相衝擊而成,對Ralf來說那是一個相當刺激的初生之犢時代嗎?
「對, 60年代末在文化上的處境是,對我們那一代來說德國並沒有當代音樂,所以我們由零開始去做,來尋找我們的音樂語言,這就是我們在那段日子所做的東西。結果我們花了近七年才做出《Autobahn》,首張電子流行樂專輯;繼而再有《Radioactivity》,全然電子聲音演奏的作品。然後我們持續下去,正如之前所說,是持續性的進程。」
對於電子音樂先鋒這個美譽,Ralf又怎樣理解呢?
「當我們開始時,我們的意念在德語中來說是想創造一種folk music──電子紀元的folk music、一種industrial folk music,這是當時我們的願景。來到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時,出來的音樂就是這模樣了,於是我們在世界各地的文化層面取得了迴響。回到60年代末時,我們只是在Düsseldorf的細小場地表演;然後我們走到歐洲各地如法國、比利時、荷蘭、英國;現在我們走遍全世界玩奏我們的電子音樂,取得妙不可言的迴響,這令我們取得能量繼續創作。」
Kraftwerk在1970至73年間的頭三張Krautrock紀元專輯《Kraftwerk》、《Kraftwerk 2》和《Ralf & Florian》一直沒有以官方形式再版成CD,有傳其original masters已遺失了之故,亦有傳Ralf和Florian不喜歡這些早年的作品而拒絕再版。但原來兩個說法都不是真的。
「Master tapes已準備好,並已為技術性的品質處理展開工作。現時坊間的全是Bootleg。但我們要忙於巡演開音樂會、為新作工作,所以有待未來日子,我們才會再推出這些舊唱片。」
Kling Klang與聲音設計
聽了Kraftwerk多年,對他們的音樂考究再考究,最終我發現其音樂的一大別樹一幟的重要之處,是他們開拓了聲音設計(sonic design)的理念,把平面的聲音做出立體的效果。
「對,這是來自Kling Klang的意念。德文中,Klang是聲的名詞,Kling是聲的用字,Kling Klang有發出聲音之意(像”Ding-Dong”般),也參考了『陰陽』的含意,聲音的不同元素。這是Kraftwerk與Kling Klang製作的概念。」Kling Klang,又即Kraftwerk的私人錄音室及自家品牌名字也。
去年一眾當今的Chiptune / Bitpop / 8-Bit電音製作人「以古老8-Bit電子遊戲系統演奏Kraftwerk作品」帶來了一張致敬合輯《8-Bit Operators》,Ralf對於8-Bit電音運動有何評價?
「這就是我們在〈Pocket Calculator〉所帶出的另一願景,你可以用所有小型玩具配以電腦來創作電子音樂,是流動性的概念。」
樂迷最關心,是Kraftwerk到底何時會為繼2003年《Tour de France Soundtracks》後的全新專輯動工呢?
「我們一直有為專輯工作,已有了意念,當我們回到Kling Klang錄音室時便會為Kraftwerk的下一張專輯動工。」
有說Ralf Hütter的老拍擋Florian Schneider做訪問時每每會予人古怪而令人費解的回答,幸而今次我跟Ralf的二十分鐘對話,他都回答得很實在,除了我問到他現在喜歡聽甚麼類型的音樂時。
他回答:「我們聽噪音,以及來自宇宙及各處的環境聲音。」